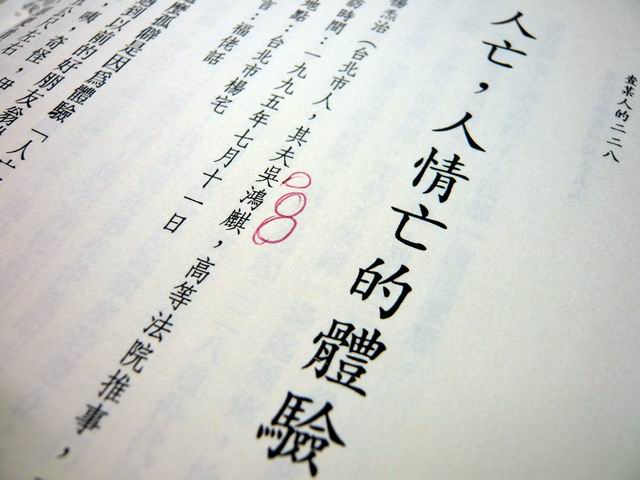黃碧珠為高雄警員蘇進長的夫人,她說……伊被槍殺時,那早上,我囝仔揹著,準備要去前津派出所面會伊,但是,伊舊城派出所的同事,不讓我一個人自己去,堅持叫一個人跟我一起去。結果在半路上,公共汽車壞去,那個陪我去的警員,才跟我講,阮先生已經被槍殺。我就趕快趕去前津派出所,去時伊已經死了。我就買一個「面桶」(臉盆)和一條面巾,把伊面洗洗的,四處擦擦。伊的面都是血。當天,就叫「土公」(辦喪事的人),直接把伊送去埋葬。
後來,經過十幾年,我又再結婚,生活不好,無法度,就再結婚。那是經人介紹的。結婚以後,有一個查甫囝仔。但是無幾年,我就又離婚,伊無愛出去賺吃,又愛賭博,我離婚較自由。我就自己照顧囝仔,後來,查某囝仔長大嫁人,查甫囝仔也有工作,娶某,生活普通啦。
沈秀華,1997,"艱苦扶孤的警察太太-黃碧珠(其夫蘇進長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p.46-47。
蘇白勉其夫蘇水木,八堵火車站副站長。 阮頭家二月被人抓去,四月我才生最小的查某囝仔,彼時我自己在厝生,自己剪臍。當時生活真壞,我只好把囝仔送人;有人無生囝仔,知道我生活困難,就來向我分囝仔,我是有囝仔無法度養,也不可能賣囝仔,只好把囝仔送人,我對來分囝仔的人講:「你們就要疼我的囝仔,你若無把我疼,我就要把囝仔討回來,他們的老爸若有回來,再出去「吃頭路」(做工作)賺錢,我就拿一些錢補你們,我要將囝仔帶回來,嗚……(談及此,蘇女士傷心流淚)。」
後來我前前後後在二、三年內送三個囝仔給人,二個查甫、一個查某,都分在無遠的所在,一個查甫分去暖暖,另外一個查甫分在八堵,那個查某囝仔是分去瑞芳。
沈秀華,1997,"對天呼喚的副站長夫人-蘇白勉(其夫蘇水木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p.53-54。
平時我會對我的囝仔講:「二二八,你們老爸被叫去就無回來。」啊!嗚……(蘇女士難過出聲),我那些較大的囝仔聽我一講,也會「號」(哭),會對我講:「咱們又無怎樣,怎麼被叫去就無回來。」
我是一直想日本時代,口供問問就回來,也無想到伊會被叫去就無回來,我想這個政府怎麼會無問個口供,好人也抓抓去,壞人也抓抓去。 沈秀華,1997,"對天呼喚的副站長夫人-蘇白勉(其夫蘇水木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55。
在阮頭家被抓去二、三個月內,我不時也在夢到阮頭家,夢到伊回來,坐在眠床邊,對我講伊是被誣賴,伊也不願這樣死去。彼時有一段時間,暗時(晚上)我門口埕都不敢出去,我會把門口埕看成大坑,想腳一踏出去,就會跌下去,彼時大概是目屎流太多,目睭變不好去。
沈秀華,1997,"對天呼喚的副站長夫人-蘇白勉(其夫蘇水木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56。
楊 治,其夫吳鴻麒,高雄推事。
治,其夫吳鴻麒,高雄推事。 吳鴻麒是3月12日在高等法院上班時失蹤的,伊12日無回來,我13日就去高等法院問人,法院的人解釋給我聽,講:「二個便衣的人來請伊,講是柯參謀(指柯遠芬)叫伊去。」伊是現職在法院失蹤的,法院也有責任,也是全力在找人,我也四處在找人,到16日下午,我已經找得真失望,從法院要回來厝的路上,一路心內想講:「難道真會被滅屍,要是能讓我見伊一目也真好。」
沈秀華,1997,"人亡,人情亡的體驗-楊

治(其夫吳鴻麒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60。
回到家後,就一直流血
講也奇怪,伊一被送回到阮日本厝的圍牆旁,就一直流血不止,我就在阮厝前門口埕幫伊洗喔!擦喔!我一邊幫伊洗,一邊罵伊講:「你平時是那麼衛生的人,現在全身軀都是灰塵。」伊的兄弟幫伊換好衫以後,才搬進來厝內,要搬入來厝內時,伊還一直在流血。對伊流血的代誌,我到現在還一直無法度了解,常常問醫生:「人若一死,不是血就會凝了,為什麼伊已經死三天了,還一直在流血。」 我當時一直想不通,為什麼伊是那麼盡忠的人,會發生這種代誌,我就一直這樣想長、想短。
沈秀華,1997,"人亡,人情亡的體驗-楊

治(其夫吳鴻麒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p.64-65。
吳鴻麒死去以後,我是感覺我不止是死去一個尪婿的悲傷而已,也失去一個良師。伊比我冊讀得多,經驗也較豐富,伊死去以後,我感覺真失望,失去一個老師。
阮二人,講正經的,常常代誌要論到底才甘願。二、三年前,有人問我:「你到何時才會忘記吳先生的代誌。」我講:「這件代誌,我是永遠無法度忘記。」我常常見景生情,常常想不開,常常想伊還在我的身邊。伊回來時流的血,到這時醫生還不會解決。我是想,伊死時,無看到任何親人,可能是真難過,一回到厝,見到我的手,才流出活血。我現在都解釋成,伊永遠活在我身軀旁,讓我能夠得到真安慰。
我是想伊死時,伊的精神是留在伊的血內,回來到厝,就流在我的身軀。我摸伊時,伊的血一直流在我身軀,永遠留在我心內,就是這樣,到現在我才會一直很清楚記得這件代誌,常常想伊還活著。 沈秀華,1997,"人亡,人情亡的體驗-楊

治(其夫吳鴻麒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p.75-76。
楊 治受高等教育,看破人情世故,有堅強的孤立人格。
治受高等教育,看破人情世故,有堅強的孤立人格。 過去這四、五十年來,經濟上,吳家兄弟無人幫我,我也不要讓人幫助我,我要靠自己。吳鴻麒死後,看一些朋友、親戚那樣對待我,使我看破人情,那真是冷到腳底去。
無尪是無地位,尤其是客家人,寡婦是給人看不起的。這四、五十年多,我經濟上還過得去,吃最多苦的是人情上的苦,我無向人伸手要求幫忙,就已經被人隔得遠遠,叫我如何不看破人情。從那開始,到現在我都還留著一個真壞的習慣──「走路不看人」,只是不要跌倒就好。我常常就用批判的眼光來看人世。
沈秀華,1997,"人亡,人情亡的體驗-楊

治(其夫吳鴻麒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8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