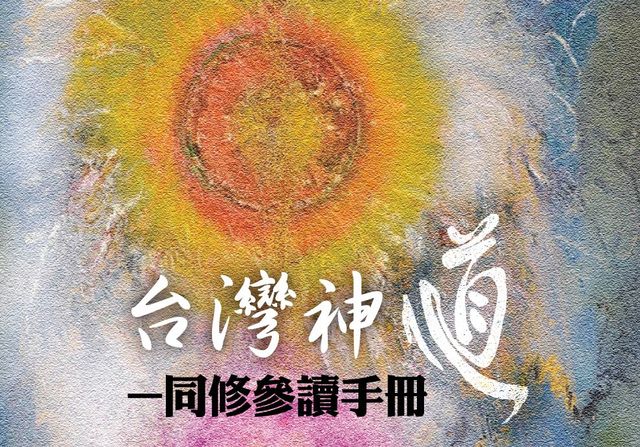文史工作者,台大中文系畢業,現就讀政大台史所。曾任職《自由時代週刊》和《黑白新聞週刊》。長期研究戰後台灣人權和白色恐怖,旁及對台灣史的種種思考。本系列專欄文章,都可視為作者的「台灣懺悔錄」。
戰後的台灣,有一個非常詭異的歷史時空,那是一個生死交錯、陰陽同悲、人鬼共愁的時代。不僅殺戮最為血腥、受難最為極端,連冥界也哀怨不安。那就是二二八。
二二八的災難是極端性的,如果要做比喻,那就是投在戰後台灣史的一顆原子彈。不過二二八原爆的災情,被當局長期掩蓋,懸為厲禁,只能化為私密的口耳相傳。即使如此,1987年後在民間人士的發掘下,出土的部分真相,仍令人感到無比震撼。
二二八的屍體意象要深入了解二二八,必須研讀民間的口述史。傳統的學術研究有時隔了一層。有些爭論集中在究竟是幾千人死亡,還是幾萬人死亡?這種爭論試圖將二二八的災情量化,結果就是王曉波的那句「名言」:「和蔣介石在大陸清黨殺40萬人相比,二二八殺2萬人是小case。」
事實上,二二八的災情不是人數統計問題,而是人權侵害問題。重點不是「死了多少人」,而是「人怎麼死的」。如果知道人怎麼死的,那可是大大的case,其慘絕人寰的程度,比蔣的清黨,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大致來說,二二八的殺戮可分為「無差別屠殺」和「捕殺」(包括隨機捕殺和計劃補殺)兩種。前者是在街頭掃射民眾,後者是將人帶走後殺害。前者固然有使用「達姆彈」這種殘忍武器,但仍不及後者血腥,因為從種種口述史料來看,捕殺與虐殺無異。
虐殺不是給一兩顆子彈而已,而是施虐後殺害,使其死於劇苦。這一點,必須從口述史中,家屬對於親人屍體慘狀的描述始能得知。他們或被鐵絲穿掌,或被割去耳鼻生殖器,或被亂刀刺死。嘉義南靖糖廠的會計陳顯宗,家屬驗屍時發現他身上有36處刀傷;基隆一位黃姓醫生,在礦坑驗到一具全身有50幾處刀傷的八堵人屍體。
從犯罪心理學來看,蔣介石的軍隊顯然以刺殺取樂,而且經過長官的鼓勵或默許。否則只要稍祭軍紀,不可能如此虐殺無度。
蔣軍除了殺人外,也積極劫財,完全是土匪的行徑。或是侵入民宅打劫,或是攔劫路人,或是綁架勒贖,或是虐殺兼洗劫。許多口述史提到,家屬在為親人收屍時,發現他身上所有錢財、戒指、手錶、皮鞋、西裝、外套全都不翼而飛,僅剩內衣褲甚至內褲。
以上所述,只是二二八悲劇的一小部分。由於悲劇太過慘烈,以致口述史充滿各種跟屍體有關的意象:尋屍、腐屍、殘屍、屍臭等。當時台北市的植物園,飄盪的不是花香,而是屍臭;基隆港、淡水河、新店溪更漂浮著大量屍體。由於這些人都是橫死,靈魂無法安息,因此在「屍體意象」之外,直接牽動的就是「鬼魂意象」。這是二二八口述史的兩大特色。
 七月是一個慎終追遠的月分,幽冥眾生也有他們應享的福利。圖為嘉義監獄一景。(黃謙賢攝)二二八的鬼魂意象
七月是一個慎終追遠的月分,幽冥眾生也有他們應享的福利。圖為嘉義監獄一景。(黃謙賢攝)二二八的鬼魂意象例如1947年3月在嘉義火車站前分三批被槍殺的16人中,筆者所見,就有陳復志、蔡金爝、盧鈵欽的家屬有靈異描述。陳復志(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)之妻蔣佩芝回憶,「七七」之前陳復志幾乎天天回來,早上雞一叫,他就走了,「回來時都不講話,我問他你被打到哪裡?傷在什麼地方?他就是不給我看,做夢似的。有天晚上我用力一掰,發現他頭上兩個洞。」
土匪兵殺了陳復志後,還到陳家搶劫,把所有值錢的東西:戒指、大衣、西裝、毛毯、毛背心、信件、書、現金等全部搜光。
盧鈵欽(市參議員、牙醫師)之妻林秀媚回憶:「槍殺當夜他的靈魂回來,在我們家後院哭了一夜…他被槍殺後,我們把屍體搬回來,放在樓下。隔天早上下樓看時,發現他雙眼眼眶紅腫得很厲害,就像是大哭過一場。」
之後過了幾個月,有一晚,五個月大的小兒子一直哭不停。林秀媚當時雇一個女孩子幫忙照顧幼兒,女孩子抱他到客廳,竟然看到盧鈵欽的鬼魂,就穿著他被槍殺時的衣服,坐在椅子上,臉伏在桌上……
蔡金爝(自行車店老闆)之子張森本(母親改嫁,從繼父姓)則說,他三、四歲時,「老式房子都掛著高高的蚊帳,我一鑽進蚊帳中,就可以看到爸爸站在外面,全身都是白的,轉著手錶,『滴滴』的聲音聽得很清楚,一直到我睡著為止。」
鬼魂入夢,常見於靈異描述。一位住大稻埕的15歲少年周吉成,2月28日當天在台北街頭被射殺。其弟周吉福回憶:「事後母親曾多次夢見三哥七孔流血的回來看她,但是一句話也沒說。」周吉成死後,周家的災難還沒結束。1963年葛樂禮颱風來襲,周家死了7個人,生活更為困苦。
又如王育霖(建中教師,林茂生創辦的《民報》法律顧問),其弟王育德在〈我的哥哥王育霖〉一文寫道:「二二八事件那年晚春的某夜,我看到他――右後頭部到左眼窩,和右太陽穴旁,有兩個空洞――很柔和的笑著走進我的寢室來,白襯衫上還沾滿了鮮血…我連忙起身問他話。『德!拜託了。』我好像聽到哥哥的嘴裡這樣說著,但一瞬間,哥哥的身影就消失無蹤了。只是一場夢罷了。」
但王育霖託給妻子陳仙槎的夢卻多了一縷哀怨。王育霖被抓走後,妻子到處尋人,李瑞漢(律師,二二八受難者)之妻也在找丈夫,便邀她搬來同住,這樣一起出門、一起找人比較方便。有一晚,王育霖倉皇入夢,劈頭就問其妻:「妳跑去哪裡,害我找不到,為什麼搬家都沒告訴我?」
陳仙槎說:「我找不到你,怎麼告訴你呢?」王育霖手指一處,說:「我住在那裡…」陳仙槎一看:栽著兩排柏樹的草皮盡頭,有一個圓圓的土丘。王育霖說:「林茂生是我的『隊長』,你去找他,就知道我住哪裡。」陳仙槎這才知道,丈夫真的死了。
人生至此,天道寧論冤死者的鬼魂,最掛念的就是至親。但至親的無限悲痛,也可能使他們提早離開人世。游美鑾談到其父游竹根(金瓜石里長):「幫父親做七的時後,每天做飯祭拜,我常聽見父親的腳步聲,一聲聲一聲聲由遠而近。」游竹根的母親不堪喪子之痛,天天哭泣,哭了一年多,哭到中風,第二年就去世了,成為二二八的隱性死亡人口。
三重周淵過的故事格外悲慘。周家被憲四團的兵闖入洗劫,並帶走周淵過。周母四處尋人找屍,光是淡水河邊,就找了不只三百具屍體。後來周淵過託夢給母親,母親才在南港橋下找到他的屍體。其弟周塗生描述當時的情景:「挖出來一看,果然是大哥。那時距離槍決日已隔了一星期,很奇怪,一見親人,屍體馬上七孔流血。」
周淵過死後,憲兵仍向周母詐財,說她兒子還活著,周母不得不四處借錢送去。最後當一切希望落空,周母每天哭泣,哭到眼瞎,最後帶病帶瘋死去。
南港橋當時埋有八個土堆,每個土堆一具屍體,當地居民稱為「八仙橋」。周塗生看到第一個土堆的死者,「死相很慘,面目全非,整張臉布滿刀痕;傷口皮肉往外翻,狀甚狼藉,難以辨識。」而吳鴻麒(高等法院檢察官,吳伯雄伯父)也在這「南港八屍」之中,全身傷痕,死相淒慘,可見先被刑求至半死,再予槍決。
其妻楊○(上毛下灬,唸招)治憶述:「屍體拖回家,一進屋內圍牆,立刻血流不止…我一邊清潔,一邊低聲對著吳鴻麒的屍體說:『你一輩子講究衛生,死時卻弄得全身灰塵泥土,髒兮兮的…』我一邊唸,一邊擦拭,血流個不停,再怎麼擦都擦不乾。」
楊女士後來是靠宗教的力量,才得以活下去。她說:「聖經羅馬書12章第19節寫著一句話:『申冤在我,我必報應。』那是耶和華幾千年前應允的話…幾十年來,我得以安靜過日子,就是這聖句。」
還有高雄的陳金能律師,3月6日在高雄市政府前被彭孟緝的軍隊射殺。其子陳木遜說,陳金能被曝屍兩、三天後,家屬才被通知將屍體運回。家屬驗屍時,發現陳金能頭部中彈,胸部、大腿各有刺刀痕跡。入殮時,陳金能死不暝目,手腳僵硬。其兄呼喚:「金能啊,你安心去吧,你的兒子由我來照顧。」屍體方才闔眼,手腳軟化,終於順利入殮。
這麼多的鬼魂意象,說明二二八的浩劫奇冤奇慘,不僅「人生至此,天道寧論」,連鬼魂也不得安寧。現在位於台北市西門町的一處商業大樓,原是日治時代的東本願寺,戰後被國民黨改為偵訊監獄,以恐怖著稱。一位在二二八被囚禁其中的歐陽可亮描述:「在白天的時間裡,面對淡水河的後院時常傳來槍聲。不用說,一定是槍決…甚至曾經謠傳,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。」
世間不平,鬼魂不寧。世人常以刻板眼光來看鬼魂,事實上,人的凶險更甚於鬼。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,多少鬼魂仍然在人間飄盪,冤不得伸?這些死於國家暴力的人,國家應該負起責任,為他們辦大型超度法會、追思禮拜,讓他們好好安息。台灣的轉型正義不應該只有「人權」,而沒有「鬼權」,畢竟鬼魂才是這些慘案的主角。
 鬼亦有正邪,人心險於鬼,誰知道世間的影影綽綽,哪個是人?哪個是鬼?(黃謙賢攝)
鬼亦有正邪,人心險於鬼,誰知道世間的影影綽綽,哪個是人?哪個是鬼?(黃謙賢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