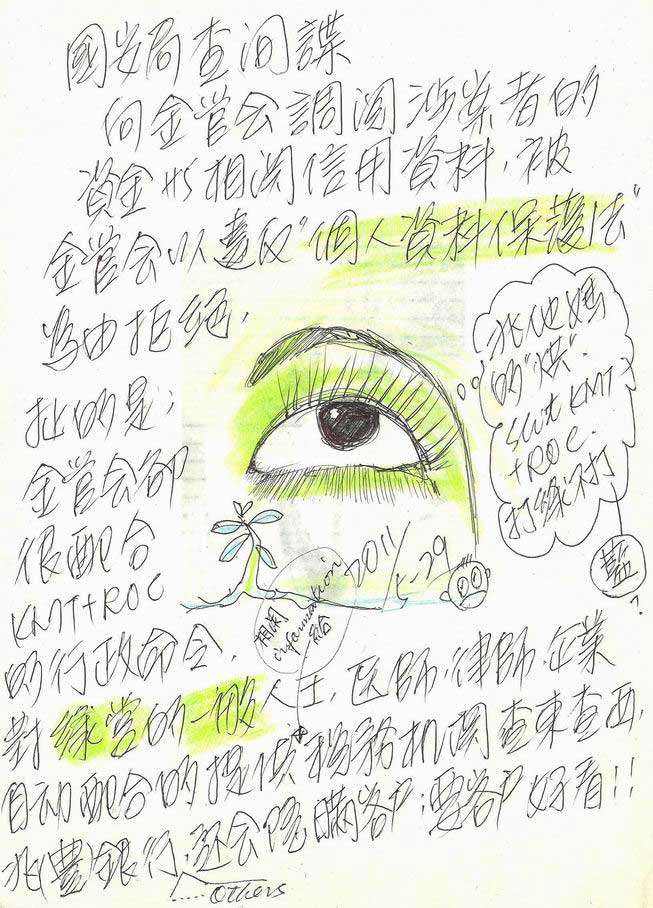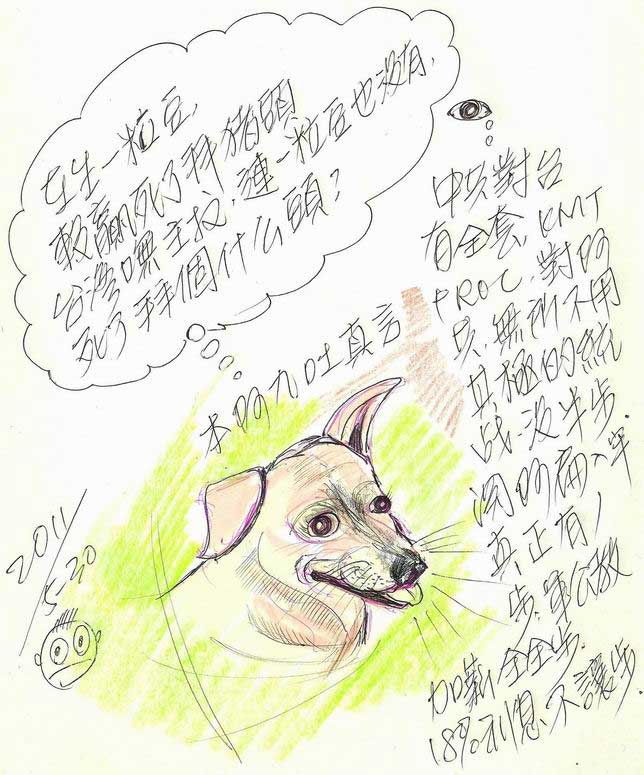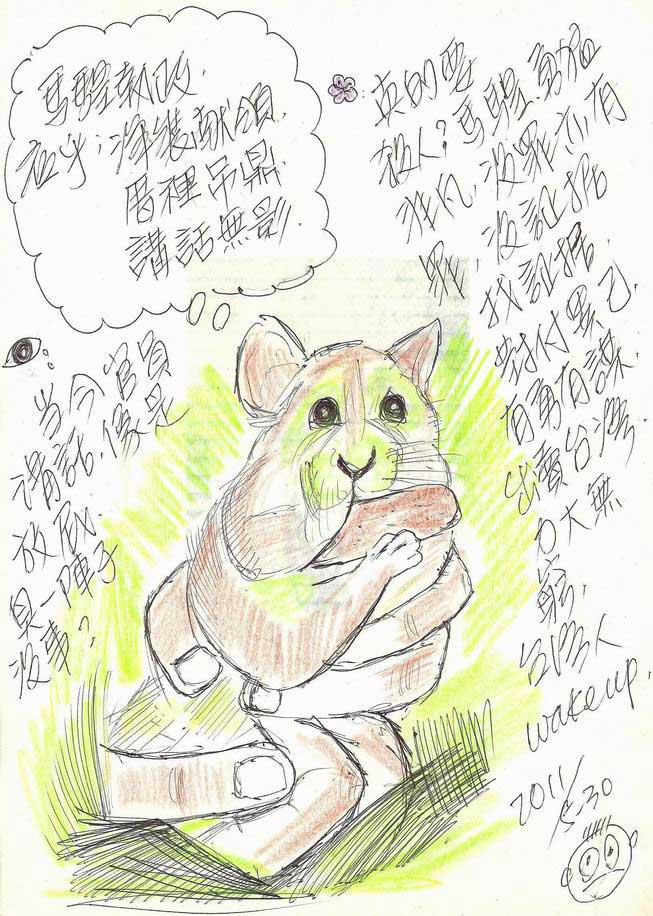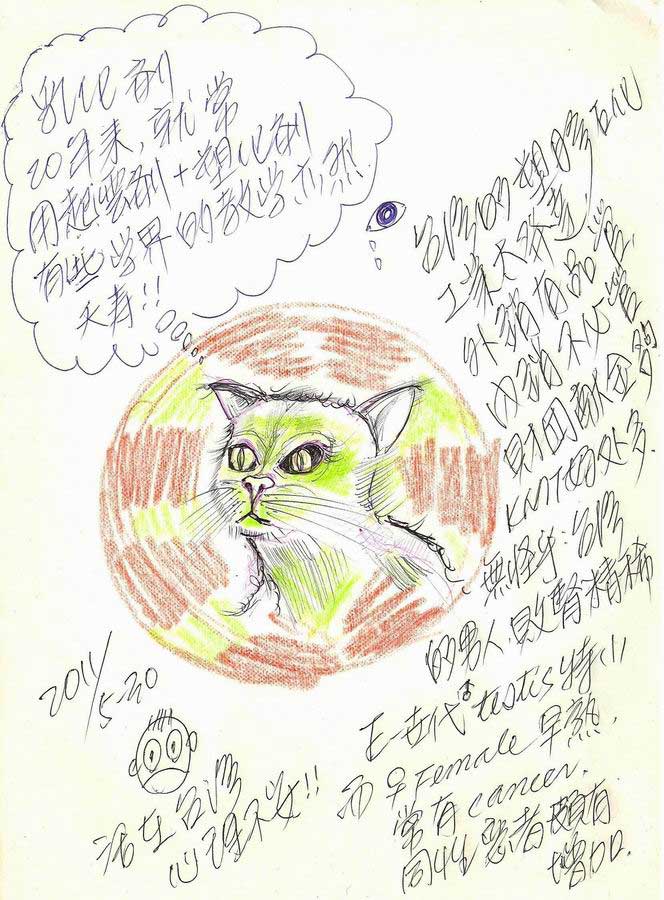新聞報導 - 楊緒東專欄
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
2011/05/31, Tuesday
 (photo source: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一書,「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」)
(photo source: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一書,「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」)
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
某隱名228遺孀。
台灣「光復」以後,我在希爾頓後面的一間公司做打字員,我曾在那裡看過中國兵仔。我看他們穿草鞋、拿雨鞋,有擔雞、有擔鴨,有擔鼎(鍋子),當時我看了驚一下。我以前看的日本兵是那麼整齊,那麼好看,那麼有勇氣,結果看到國軍是這樣,我真失望。我回去厝,還問阮老母:「為什麼咱們祖國的兵仔,穿得那樣?」阮老母講:「你不知道他們抗戰怎麼會贏?他們會飛咧!腳綁鉛。」是後來才知道是二粒原子彈,日本才會投降;也是後來才知道,國民黨也是打輸大陸的共產黨,才會來台灣。
沈秀華,1997,"踏浪的人生-匿名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84。
自二二八發生到我再嫁,這期間隔了十年。有一次,少我五歲的小弟還在金門做兵時,有一個中尉在追求我。我就對那位中尉講:「我弟弟還在金門做兵,我怎麼嫁給你?」這位中尉講:「沒問題、沒問題,我把他弄回來。」後來,阮小弟也真的自金門回來,但是我也無嫁給這位中尉。這位中尉是個外省人,我怎麼可以嫁給外省人?阮尪是被外省人打死的,我怎麼可以嫁給外省人。
沈秀華,1997,"踏浪的人生-匿名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88。
二二八事件以後,除了同事以外,我真少交外省朋友,不過我不是真要排斥外省人。他們也是無辜的,他們也不是真正的兇手。對政治方面,我真的不要「插」,但是到去年以後,有全民電台,我工作的時間都在聽全民電台,以前我聽民進黨的人在講反核,我都會想:「為什麼要反核?」但是現在聽多了,就知道為什麼要反核。
沈秀華,1997,"踏浪的人生-匿名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93。
無奈的守寡,又要為下一代的「扶養」負責,受盡風霜,受人欺侮,始終堅強,真是偉大的女性。
彼時要再嫁,是想,我會老,我的查某囝仔若無扶養好,怎麼可以,所以才會再結婚,但是……。我常會跟人家開玩笑的講:「我是踏浪而來的。」我的人生坎坷,受到很多的煎熬。在酒家受人糟蹋,再嫁,又受尪欺侮。浪有高有低,隨時變動,要能踏著浪而來,是很不容易。所以,我感覺我比一般的女孩都要堅強。我感覺我是一個很堅強、很自在的女人。
沈秀華,1997,"踏浪的人生-匿名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97。
潘罔,其夫為王添灯。我是在我15歲那年的9月14日去藝妲間。9月16日阮養母(指藝妲間的負責人)就請先生來教我學南管。從我15歲到17歲兩年期間,我就專心學南管,吃、住都是在間內。彼時,我是算賣給藝妲間做媳婦仔(養女)。在17歲那年,我就領到藝妲牌。彼時,要有藝妲牌才能出去陪酒、唱曲。以前藝妲不能賺人客(被帶出場),只能唱曲、賣藝和陪酒而已。舞女只能陪跳舞。這分好幾種,分得真清楚。
彼時,我住在藝妲間,外面酒樓、酒家宴客,若要藝妲,就會來叫阮去。當時我的藝名叫鳳嬌。我看當時那些來酒樓喝酒的人,都是高尚人,不是下流人。但是我真不願吃這種飯,常常不想出去,就被藝妲間的養母打。彼時,所有我賺的錢都要交給阮養母。
沈秀華,1997,"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-潘罔(其夫王添灯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99。
我是去添灯在新店貴德街的文山茶行唱曲、陪酒時熟識添灯的。以前茶行每年年尾都有一個總結算,總結算期間就會有三天的請客,請藝妲去陪酒、唱曲。平時有時茶販仔也會請藝妲去茶行唱曲。我就是這樣去添灯的茶行好幾次以後才熟識添灯的。後來,添灯就對我講,伊要娶我,我就應伊:「好啊!」我當時一直真不想吃藝妲這種飯,所以我就答應要嫁伊。伊當時已經有太太、亦有六個囝仔,我雖然知道要去做伊的細姨(小老婆),但是我想,這是我的命,已經遇到,就認了。彼時,我只是一直想,只要能不吃藝妲這行的飯,什麼都好(此時,潘女士聲音哽咽)。
沈秀華,1997,"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-潘罔(其夫王添灯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100。
鐵齒的王添灯身為台灣省參議員,替KMT政府主持公道,又有何罪?憲兵隊離開以後,阮小姑(王添灯之妹)來對我講:「二嫂,咱們來叫二哥跑;中國字我是不識,但是七十二計,跑為上策,我知道。」,「阮大家」(婆婆,王添灯之母)亦對我講:「阿罔,阿罔,咱們來雇船從後門跑。」阮三人就去勸阮頭家跑,伊應阮講:「我對國家盡忠,對百姓也打拼,要抓我幹什麼?」伊那種日本精神無想到中國和日本的作風是不一樣。日本時代,添灯因為參加文化協會,曾被日本人叫去問話,但是日本人對伊是高等待遇,茶啦!餅啦!不像國民黨一聲就把人捏死。阮添灯要是能讓查某人作主意就好了。伊不跑,「鐵齒」。
沈秀華,1997,"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-潘罔(其夫王添灯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105。
雖細姨還有名份,但失去男人的依靠,有名無份,只好咬牙拼生死。我雖然被逼和添灯離婚,但是我一回來士林以後,我還是有拜添灯的「神主牌」,我常常在伊的神主牌前跟伊講話,我講:「我拜你四、五十年,你到底有回來吃?還是無回來吃?你的冤枉無處講,我的冤枉也無處講,嗚……,你害我今日變成這樣,像是無人的,嗚……。」(談及此,潘女士悲從中來,傷心落淚。)關於我拜添灯的代誌,有人對我講:「阿罔,伊有伊厝的人拜,你幹什麼拜伊?」我講:「你不知道,這間厝是用伊的錢買的,我拜,拜我的心願。」
這四十多年來,我將一切放在心內,一天過一天,今日煩惱明天,明天煩惱後天無米。現在我已經老了,今日你來跟我採訪,我的苦衷終於有處講,我真歡喜(聲音哽咽)。不然,我不時常常自己坐在那裡,對著添灯的神主牌講話:「添灯阿!你和我二人的苦衷,無處可講給人聽。」我這裡的人也無人知道我的苦衷。現在還好是有真多人在講二二八,以前根本就無人敢講。我以前會怨嘆政府跟外省人,我也不跟他們講話,我曾對我的囝仔講:「我給你們自由交男女朋友,但是你們不可交外省人。」我的查甫囝仔應我講:「外省也有好的人。」我講:「對啊!但是好人都被壞人連累到了。」
二二八以後,每一次選舉,我每一個候選人都蓋給他們,一個尪這樣死去,選舉幹什麼?我也未曾對我二個囝仔講起阮頭家的代誌,他們這幾年才知道。二二八以後,我當然會驚,但是驚也無效,目睭金金(眼睜睜地)的看兵仔用槍把整厝內的物件都弄得碎碎,驚也無法度。
沈秀華,1997,"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-潘罔(其夫王添灯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p.113-114。王鄭阿妹,其夫王貴龍,八堵車站總務。
我對日本投降的代誌,也不太清楚,我是曾在後龍看過兵仔(指國民黨軍隊),他們好像是在演習,但是咱們不去動他們,他們也不會來動咱們,咱們跟那些兵仔也無什麼關係。二二八發生時,我和阮頭家差不多結婚七年,阮的查某囝仔七歲,查甫囝仔六歲。二二八發生時,我聽人講外面真亂,我對阮頭家講,叫伊不要去上班,但是伊講:「咱們又無去動人,無要緊,不會有代誌。」結果伊一去就無回來,我叫伊不要去,伊以為是像日本時代,若無做什麼壞代誌,就不會有代誌,阮頭家想,咱是老實人,又無「插」任何代誌,應該是無要緊,結果伊一去上班就被抓去。
沈秀華,1997,"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-王鄭阿珠(其夫王貴龍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119。
當時鐵路工作人員,只要身制服(黑色)就被認為與228有關,會被胡亂點名抓去槍殺。
阮頭家被抓去以後,無薪水回來要怎麼辦?豬若吃那樣,阮就吃那樣。阮有一點田,灑點稻仔,有的有出穗,有的還未出穗,厝內無得吃,我就用手去弄一些稻仔回來吃,一天弄無多少,弄得我手都破皮流血,再無得吃,就去撿蕃薯,隨豬仔吃,豬仔若吃那樣,阮就吃那樣,平時滾蕃薯給豬仔吃,阮若工作做做回來厝,腹肚餓,就先留一鼎(鍋)蕃薯在灶頭,先提蕃薯去給豬仔吃,豬在吃,阮也在吃那鼎留在灶頭的蕃薯,彼時阮都是撿蕃薯來過頓(過日子)。
沈秀華,1997,"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-王鄭阿珠(其夫王貴龍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.121。
阮頭家無回來以後,我曾去把伊「牽亡」,伊講伊二月十九日被抓去以後就馬上被打死,還交代阮二月十九日給伊作忌日,伊講伊這樣死去真不願,放二個囝仔無一個人高(指二個小孩都還小),還講伊也真不願,死時,有一個囝仔還未生好,阮頭家二月出代誌,我六月才生第三個囝仔,結果那個囝仔出世七天以後就無去,我彼時想這個囝仔若真的活了,我也無法度養伊,都無得吃,怎麼養,啊!不會講,日子是真艱苦。
沈秀華,1997,"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-王鄭阿珠(其夫王貴龍)",《查某人的二二八-政治寡婦的故事》,玉山社,台北,pp.125-126。
出處: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
http://www.taiwantt.org.tw/tw/index.php?option=com_content&task=view&id=3637&Itemid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