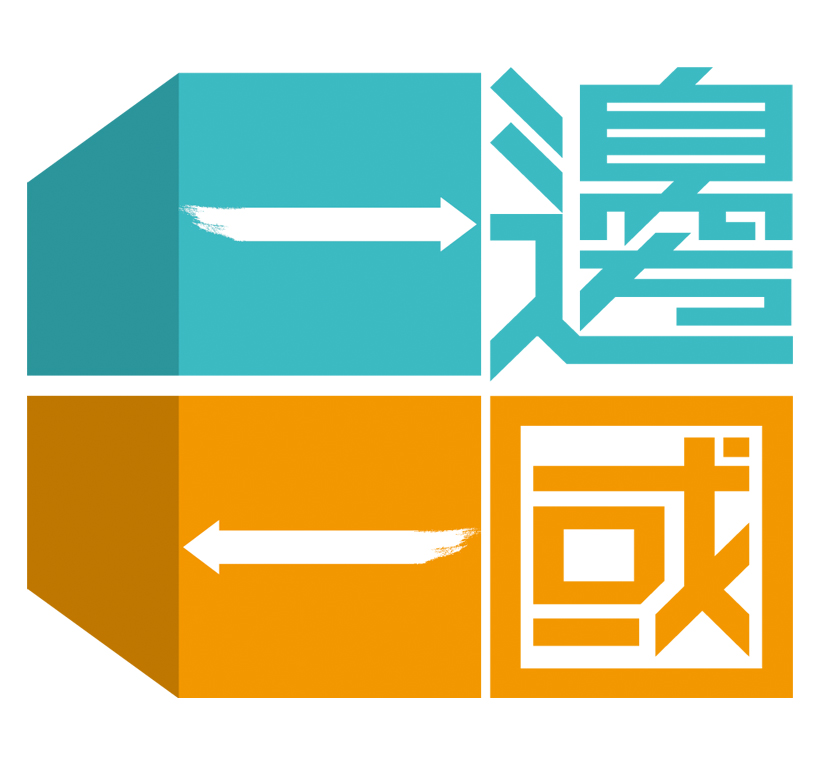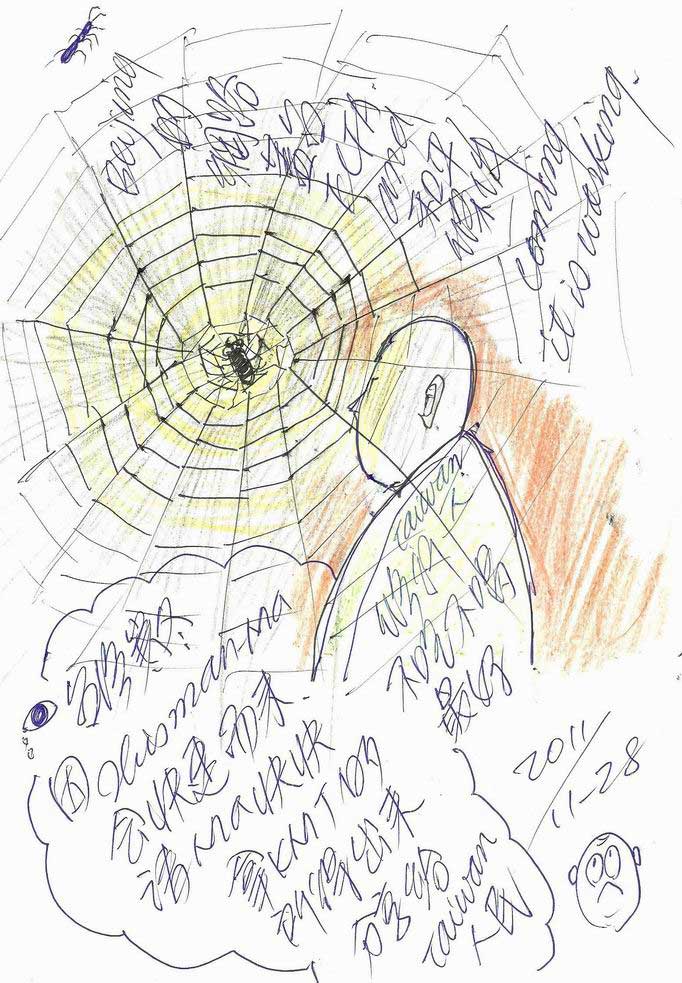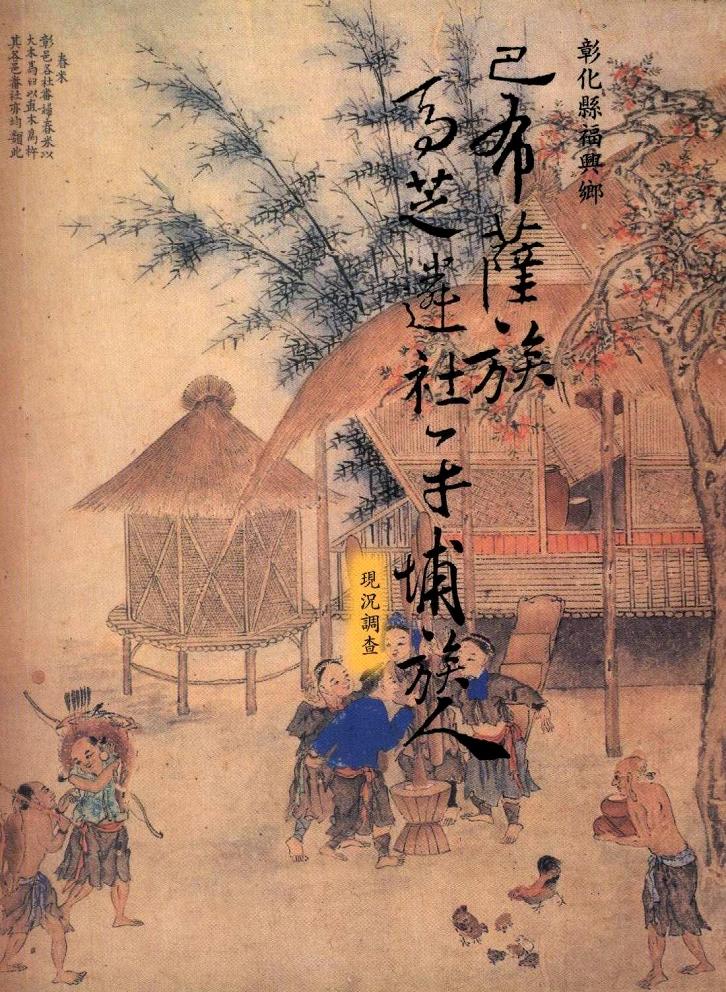作者
陳順孝
宜蘭人,種過田、擺過地攤、編過報紙頭版。 現任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、《生命力新聞》編輯人、《莫拉克獨立新聞網》共同編輯人。 繼續閱讀>>
聞自由史
《牽阮的手》上映了。這部紀錄片描述少女田孟淑(田媽媽)為了愛情違抗父命,與大她十六歲的醫師田朝明私奔結婚;婚後,夫妻倆更為了民主反抗威權政府,歷經白色恐怖、雷震與中國民主黨組黨事件、李萬居與公論報被奪事件、彭明敏與台灣人自救宣言事件、美麗島事件、林義雄家血案、鄭南榕自焚事件,始終走在第一線,公開遊行示威、秘密救援政治犯。小我的純真情愛、大我的民主奮鬥,交織成史詩般的巨作,讓我在試映會上熱淚盈眶。
我會熱淚盈眶,是尊敬田媽媽伉儷的真情和勇氣,也是敬佩導演莊益增、顏蘭權伉儷以五年時間攝製一部紀錄片的用心和堅持;此外,片中一張張歷史事件的報紙版面,更一次次讓我想起自己當年在圖書館裡,初次看到這些歷史性版面的震撼,以及自己從中得到的學習和成長。
我剛進報社當編輯時,啟蒙師父告訴我,學編輯第一年學基本技藝,第二三年逐步發展自己風格,三年之後就只能接受時代考驗,要經歷一個個歷史事件才能學會如何編輯重大事件版面,他的結論說:「新編輯永遠不如老編輯,像我們這輩編過總統蔣公逝世的新聞,那不是一個人死掉,而是一個神死掉,沒有身歷其境的新編輯永遠無法體會那種氛圍、無法學會那種編法」。
我敬佩我的師父,但覺得一門學問如果無法讓學生超越老師,一定有問題。我開始思考,新編輯就算不能穿越時空去處理歷史事件,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神入歷史情境,體驗當時氛圍?
某個夏日午後,我在報社開完會,走到街上閒逛,不知不覺逛到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,一時興起,進去查閱微縮膠片目錄,一眼看到一九四七年的《台灣新生報》,如獲至寶,迫不及待尋找那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版面,找到一讀,大為震撼。
《新生報》是當時的第一大報、也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機關刊物,但在二二八事件初期,忠實報導民眾觀點、指摘緝烟人員違法帶槍開槍肇禍,並未偏袒官方;三月十日報紙突然停刊一天,十一日復刊,立場丕變,轉而痛罵群眾是叛徒、指摘「若干含有毒素的報紙的負責人⋯⋯一味暴露祖國的弱點」是二二八的禍首、台灣的罪人。
同一家報紙,為何相隔一天就判若兩人?原來,三月八日國軍登陸,隨即展開血腥鎮壓,《新生報》社長李萬居遭軍警毆打,總編輯吳金鍊、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幹部林界、邱金山、蘇憲章、王天賞更慘遭槍殺,報紙因此在十日停刊;十一日復刊後,總編輯、總經理改由軍人出任,立場自然丕變。
我讀過一些二二八史料和多位親歷事件的報人回憶錄,對這段歷史並不陌生。然而,讀著微縮膠片上的版面,想著背後的斑斑血跡,仍然悲憤難抑,幾度對著螢幕嘆息;我雖然無法百分之百體會當時編輯的心情,但再看這些版面,看到的不再只是用字遣詞、編排技巧,而是編輯在現實情境中建構真實的艱苦血淚。
從此,我有空就進圖書館,調閱舊報紙、比對史料和報人回憶錄,從二二八事件、一九五七年的劉自然事件、六五年的廖文毅事件、七七年的中壢事件、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、八○年的林義雄家血案,以至我進報社後發生的八九年鄭南榕自焚事件,一步步重建每一個版面背後的歷史情境、報社氛圍、編寫行為。
我同樣關心這些歷史事件如何影響一個個公民的生命。例如,《新生報》總經理阮朝日女兒阮美姝苦尋父親下落五十年,直到一九九七年,曾任警備總部司機的警界退休人員才透過友人告訴她,她父親當年和總編輯吳金鍊一起被載往六張犛山上槍決。
又如,與田媽媽伉儷相交甚篤的李萬居,二二八事件後被迫離開《新生報》,另創《公論報》,《公論報》發行量曾是民營報之首,但總主筆被捕下獄、廣告主被「勸退」,公司經營困難;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趁機入股,與李萬居爭奪經營權,法院初審判決李萬居敗訴,李萬居須繳二百萬元擔保才可免予假執行,民眾為此發起「援助公論報運動」,籌足二百萬,但一夕數變,未把錢送進法院;《公論報》終於被奪,只留下李萬居的名言:「辦報是一種社會服務、一種犧牲」。
因此,當我觀看《牽阮的手》時,不僅隨著劇情見證田媽媽夫婦的真情、理想和勇氣,也藉由扎實史料和寫實動畫,重新理解雷震、李萬居、林義雄、鄭南榕等等民主前輩的理念、奮鬥和犧牲,我還藉著片中不時出現的歷史事件版面,體察記者、編輯在理想與現實、記實與避禍兩難間掙扎的艱辛。
對我來說,《牽阮的手》記錄的,不是消逝的往事,而是深刻反映權力面貌、人民意志、人性尊嚴的不朽篇章;這樣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時間、任何空間。舉例來說,奪取公論報和關罰艾未未,不都是獨裁政權對異議的壓制嗎?捐款救公論報運動和借錢給艾未未熱潮,不正同樣反映人民意志嗎?李萬居和艾未未的不屈不撓,不正同樣展現人性尊嚴嗎?
我覺得了解權力面貌、人民意志、人性尊嚴才能做好新聞報導,才能從賣弄文字技巧、耍弄編排技藝的「文字匠」、「編輯匠」,進化成能夠直指事件核心、探索新聞意義的「新聞人」、「編輯人」;我更認為,唯有了解今天的政治民主、新聞自由如何得來,才能真正珍惜自由、不濫用自由、進而捍衛自由。而要了解這些,《牽阮的手》是最生動、最深刻的教材。
我會熱淚盈眶,是尊敬田媽媽伉儷的真情和勇氣,也是敬佩導演莊益增、顏蘭權伉儷以五年時間攝製一部紀錄片的用心和堅持;此外,片中一張張歷史事件的報紙版面,更一次次讓我想起自己當年在圖書館裡,初次看到這些歷史性版面的震撼,以及自己從中得到的學習和成長。
我剛進報社當編輯時,啟蒙師父告訴我,學編輯第一年學基本技藝,第二三年逐步發展自己風格,三年之後就只能接受時代考驗,要經歷一個個歷史事件才能學會如何編輯重大事件版面,他的結論說:「新編輯永遠不如老編輯,像我們這輩編過總統蔣公逝世的新聞,那不是一個人死掉,而是一個神死掉,沒有身歷其境的新編輯永遠無法體會那種氛圍、無法學會那種編法」。
我敬佩我的師父,但覺得一門學問如果無法讓學生超越老師,一定有問題。我開始思考,新編輯就算不能穿越時空去處理歷史事件,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神入歷史情境,體驗當時氛圍?
某個夏日午後,我在報社開完會,走到街上閒逛,不知不覺逛到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,一時興起,進去查閱微縮膠片目錄,一眼看到一九四七年的《台灣新生報》,如獲至寶,迫不及待尋找那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版面,找到一讀,大為震撼。
《新生報》是當時的第一大報、也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機關刊物,但在二二八事件初期,忠實報導民眾觀點、指摘緝烟人員違法帶槍開槍肇禍,並未偏袒官方;三月十日報紙突然停刊一天,十一日復刊,立場丕變,轉而痛罵群眾是叛徒、指摘「若干含有毒素的報紙的負責人⋯⋯一味暴露祖國的弱點」是二二八的禍首、台灣的罪人。
同一家報紙,為何相隔一天就判若兩人?原來,三月八日國軍登陸,隨即展開血腥鎮壓,《新生報》社長李萬居遭軍警毆打,總編輯吳金鍊、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幹部林界、邱金山、蘇憲章、王天賞更慘遭槍殺,報紙因此在十日停刊;十一日復刊後,總編輯、總經理改由軍人出任,立場自然丕變。
我讀過一些二二八史料和多位親歷事件的報人回憶錄,對這段歷史並不陌生。然而,讀著微縮膠片上的版面,想著背後的斑斑血跡,仍然悲憤難抑,幾度對著螢幕嘆息;我雖然無法百分之百體會當時編輯的心情,但再看這些版面,看到的不再只是用字遣詞、編排技巧,而是編輯在現實情境中建構真實的艱苦血淚。
從此,我有空就進圖書館,調閱舊報紙、比對史料和報人回憶錄,從二二八事件、一九五七年的劉自然事件、六五年的廖文毅事件、七七年的中壢事件、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、八○年的林義雄家血案,以至我進報社後發生的八九年鄭南榕自焚事件,一步步重建每一個版面背後的歷史情境、報社氛圍、編寫行為。
我同樣關心這些歷史事件如何影響一個個公民的生命。例如,《新生報》總經理阮朝日女兒阮美姝苦尋父親下落五十年,直到一九九七年,曾任警備總部司機的警界退休人員才透過友人告訴她,她父親當年和總編輯吳金鍊一起被載往六張犛山上槍決。
又如,與田媽媽伉儷相交甚篤的李萬居,二二八事件後被迫離開《新生報》,另創《公論報》,《公論報》發行量曾是民營報之首,但總主筆被捕下獄、廣告主被「勸退」,公司經營困難;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趁機入股,與李萬居爭奪經營權,法院初審判決李萬居敗訴,李萬居須繳二百萬元擔保才可免予假執行,民眾為此發起「援助公論報運動」,籌足二百萬,但一夕數變,未把錢送進法院;《公論報》終於被奪,只留下李萬居的名言:「辦報是一種社會服務、一種犧牲」。
因此,當我觀看《牽阮的手》時,不僅隨著劇情見證田媽媽夫婦的真情、理想和勇氣,也藉由扎實史料和寫實動畫,重新理解雷震、李萬居、林義雄、鄭南榕等等民主前輩的理念、奮鬥和犧牲,我還藉著片中不時出現的歷史事件版面,體察記者、編輯在理想與現實、記實與避禍兩難間掙扎的艱辛。
對我來說,《牽阮的手》記錄的,不是消逝的往事,而是深刻反映權力面貌、人民意志、人性尊嚴的不朽篇章;這樣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時間、任何空間。舉例來說,奪取公論報和關罰艾未未,不都是獨裁政權對異議的壓制嗎?捐款救公論報運動和借錢給艾未未熱潮,不正同樣反映人民意志嗎?李萬居和艾未未的不屈不撓,不正同樣展現人性尊嚴嗎?
我覺得了解權力面貌、人民意志、人性尊嚴才能做好新聞報導,才能從賣弄文字技巧、耍弄編排技藝的「文字匠」、「編輯匠」,進化成能夠直指事件核心、探索新聞意義的「新聞人」、「編輯人」;我更認為,唯有了解今天的政治民主、新聞自由如何得來,才能真正珍惜自由、不濫用自由、進而捍衛自由。而要了解這些,《牽阮的手》是最生動、最深刻的教材。